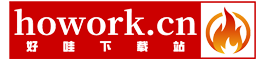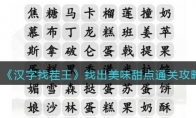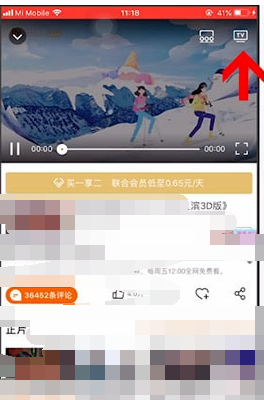贾平凹的《废都》对女儿浅浅的裤裆诗有影响吗
父书女读,肯定影响比别人要深刻!…《废都》初成,就被“禁”,就是怕有不好的影响。果然,父传女效,当上了“诗人”的女儿,先受到了其父《废都》的负面影响,遗传性地写出了“寂寞无聊”时玩“黄瓜”,做游戏时,玩“屎、尿”,而且,你尿得“是一条线”,我尿成“一个坑”……作家创作,不能不慎重啊!作品是让人看的,必须严肃,存有敬畏之心!
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中从败退回来龙文章犯了什么罪
龙文章犯了什么罪?死罪。虚冒军官,拒不听令,临阵脱逃,哪一条都是死罪,三条加起来就是罪无可赦。但这一切都有个前提,就是军法能被认真执行。但在国伍里,军法就从未被认真执行过,体现的向来只有长官意志。在《团》剧中,长官就是虞啸卿。虞要龙文章死,龙必须得死,虞不要龙死,龙就想死也死不了。孙元良南京战役临阵脱逃,跑到躲了起来,后来不是不了了之?昆仑关战役,第九师撤退时被打了个稀里哗啦,师长郑作民被炸死,副师长夏德贵跑了个踪影全无,后来第九师被委员会取消,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无名师,夏德贵怎么处分的?记了个大过就完了。常德会战,第十军救援五十七师余程万部,第三师在进攻德山时溃败,师长周庆祥带着师部一帮人跑没了踪影了,等到日军撤退后才又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。周庆祥被怎么了?什么事都没有。第三次长沙会战,鲁道源新编第十师师部在影珠山遭日军袭击,鲁道源扔下部队不管,只身跑到后方,待友军救援形势稳定后,鲁才跑了回来,军长孙渡斥责了鲁一番,但也就是斥责而已,鲁没有受到任何惩罚,后来还接了孙渡的军长职务。第二次长沙会战,第七十四军从浏阳蕉溪前往黄花市的途中,遭日军突然袭击,全军除五十一师外,另两个师伤亡近半,最惨的是第五十八师,后来追究责任,薛岳说问题出在第二十六军萧之楚掩护不力,但最后却把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给枪毙了,说是临阵脱逃,萧之楚却一点事也没有,但再后来当时的参谋处长赵子立等多名当事人证实,问题不在任何人身上,而在薛岳身上,是他的军事部署有问题,据赵子立所言,战时的电讯稿、命令等各种文件均可作为佐证,但薛除了几句自责的场面话,会没有给予任何处理。最为讽刺的是,廖被枪毙后,又马上被被证实是枉杀,会又发文对家属表示慰问。有没有罪,该当何罪,没有定理,都由当权者的想法与心情决定。龙文章是虚冒军官,但这么做是为了把溃散在的散兵游勇收容、组织起来,不是为了邀功谋利,这个往积极的方向理解,就是自告奋勇、挺身而出;龙确实临阵溃逃,但临的什么阵?没有谁给他任务,下达什么指令,龙是自己找来的一场仗打,同样往积极的方向去看待,这是激于大义,舍身杀敌。龙在败局已定,打下去就是为死而死的情况下,率兵撤逃,同样往积极的方向去考虑,是避免无谓牺牲,保存有生力量。坐实了的,不可解释的,就是拒不听令。虞要龙文章,龙却耍了个花枪,借着炮战地遁了。这是最不能容忍的。后来虞啸卿对龙文章有万种不满,各种理由的,但归结起来,就是一条:不能无条件执行命令。虞啸卿要的是军令如山倒,所有人都成为他的枪杆子,打枪的就是他一人虞啸卿,而枪杆子是不能有想法的,喊开火就开火,看停火就停火,枪坏了就弃之不顾。这样的枪其实就是炮灰的另一个名称。但龙文章却有想法。龙反复考虑的,就是得打有意义的仗,可以,但不能死的不明不白。国难当头,家国沦丧,军人尤其要,但不能不明不白,像炮灰那样。这样的想法并不高深,说白了就是,最卑微的人也是人,不是垃圾,不是炮灰,他要死也得像人那样。但这么个不怎么高深的说法,是不被虞啸卿认同的。他只关心自己的雄心壮志,骨子里视所有的部下如草芥。而这样的部下中,若有人有令不从,不死,这是决不能忍受的。这种所谓的雄心壮志,名目上轰轰烈烈,冠冕堂皇,骨子里与野心,与对权利的征逐,是紧密勾连的,看上去是烟火般漂亮,但总是被阴暗物质所包裹。对更多的人来说,是要守疆卫土,但更是一种力量,是可以获得更大力量的一种力量。在此意义上来说,虞啸卿自觉不自觉地在玩起来了政治,这种政治就是权谋。龙文章当死,无他,就在于不听令。因为他居然没有听虞啸卿的命令临阵脱逃,像条狗一样逃回来了。但虞没杀他。没杀不是罪名不够,更不是不想杀,而是龙还有可利用的价值。剧中孟烦了说得很清楚,虞没杀龙,让龙来当川军团团长,是在玩移花接木的把戏。这是龙能活下来的最根本原因。如果还要说得好听点,就是虞还有点惜才之心,但这里照样有个前提,就是龙能对自己“令行禁止”(唐基就是这么说的)。可惜的是,龙文章总是对命令打折扣,提要求,有多余想法,不断拆台,让虞不厌其烦,深恶痛绝。这样的一个人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。龙文章就是导演一个想法的具象化,一个理想的化身,只能活在电视剧中,像剧中那样能在洞穴深处,日军营垒中那样活个三十来天,只能说这是在用《神雕侠侣》的手法处理故事。对这个导演可能也没办法,因为大家都想看到这样的事,俺也是。
鲁迅有哪些一般人不知道的秘密
鲁迅是1949年以来被研究最多之人,鲁迅研究是显学,上世纪80年代就能给博士头衔了,可说没有什么秘密了,但受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氛围影响,对鲁迅的一些 生活细节说的很少。首先,鲁迅很有钱吗?受陈明远一些文章影响,今天很多人都说鲁迅很有钱。其实鲁迅一生收入不高,他在北洋教育部时,固然收入不错(没月300多大洋),但职务不高。袁世凯请曹汝霖当部长,许以月薪2000大洋,曹仍抱怨比自己当律师挣得少(见《九十老人自述》)。胡适给军阀写一篇文章,即有5000大洋,此外,胡适一度掌握庚款下的部分资金发放,与他们相比,鲁迅收入不算太高。更麻烦的是,这些钱经常拖欠,鲁迅编杂志写稿,常是义务劳动,据许广平记,鲁迅晚年穿的还是留学时穿的裤子。其次,鲁迅为什么老去日本医院?据鲁迅日记,鲁迅先后与30多名日本医生、护士接触过,因为他自己在日本学过医,而当时日医价格便宜,且受德国影响,全科为主,而不是欧美提倡的专科,比较亲切、方便。符合鲁迅当时收入情况。其三,鲁迅是革命家吗?这是后来冯雪峰等人神话的结果,鲁迅给延安拍电报、送火腿之类,可能都非鲁迅创意。鲁迅加入左联,一是他晚年确实倾向革命,二是被创造社围剿,自己有危机感,怕成为落伍者,成为局外人,三是左联名义上奉他为盟主。鲁迅与左联产生过许多摩擦,鲁迅对只谈革命的文学不太认可,他坚决拉郁达夫入左联,但郁还是被开除,郁也发声明说主动离开左联。其四,鲁迅脾气暴躁吗?鲁迅和郁达夫、许寿裳、蔡元培等人保持了终生友谊,但和胡适、钱玄同、林语堂发生纠纷,特别是与周作人之间产生矛盾,这中间可能有性格问题。鲁迅和许广平谈恋爱时,一次喝醉了酒,曾将许脑袋按在桌上,当时他刚和周作人闹翻,临时租在砖塔胡同俞芳姐妹的院子里,酒桌上还用拳头打了俞芳的拳头,俞芳遂避席。上世纪80年代,曾有学者采访俞芳,以当时氛围,俞芳自然只说鲁迅好的东西。其五,鲁迅对不起原配吗?鲁迅与原配朱安有过性行为,据郁达夫说,鲁迅为控制,冬天只穿单裤。当时留学生面对旧式婚姻多采取鲁迅式态度,鲁迅所为并不过分,胡适四处留情,也难说是道德典范。这是特殊时代下的特殊困境,无可奈何。其六,鲁迅是文坛盟主吗?鲁迅成名晚于周作人,周作人一度领袖文坛,一是他外语好,翻译上贡献大,二是他阅读量大,对世界文学更了解。他是京派开山之祖,沈从文是第四代,林徽因等人是第三代,废名等人是第二代。周作人扶持过很多人,但他性格疏懒,不愿参与组织工作。鲁迅编杂志、推新人、提口号,或有争文坛地位的意思。鲁迅的文章当然很好,但耽于对骂,严肃创作不多,小说中好坏参半,盟主是左联赏的,当时真正有学问的人这么看的,恐怕不多。
史书记载霍去病的死用“卒”,霍光的死用“薨”,是什么原因
很高兴和大家聊聊关于古人的丧葬礼仪。古代时候,随着身份和地位的不同,对其死亡的称呼也大不相同。《礼记》中这样规定的:这么多的死法,如何称呼要根据去世者的实际情况而定。同时,史家的立场和观念非常重要。我们先来看一下《汉书·霍光传》,这是《汉书》中的经典名篇,大家搞历史的,搞政治的,必须要读《霍光传》。《汉书·霍光金日磾传》是这样描述关于霍光的葬仪:对于霍光的死,史家用了“薨”这个字眼。按道理来说,霍光并不是诸侯王,刘邦曾经立过祖制:“非刘姓而王者,天下共击之”。霍光给汉朝打工,应该属于“大夫”,他的死应该称为“卒”才对。但是,我们看下文,汉宣帝很重视霍光的葬仪,他安排了重臣办理丧事:注意看霍光的殡葬仪物:1.“璧珠玑玉衣”――这是天子死后穿戴的,比那个马王堆墓的“金缕玉衣”还要高一个档次;2.“梓宫、便房、黄肠题凑各一具”――这也是天子的规格。天子所赐,为梓宫,自己搞的,那叫梓棺。“黄肠题凑”可不同于一般的“题凑”,“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,故曰黄肠。木头皆內向,故曰题凑。”在两汉时期,殡葬崇奢之风十分严重。但富户们再有钱,死了也只敢使用“题凑”,而不敢使用“黄肠题凑”,那是严重的“僭制”,敢胡来,拉你一家子去菜市口开刀。3.“载光尸柩以辒辌车,黄屋在纛”――辒辌车和黄纛,这也是天子的规格。4.“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”――动用了国家正规军士,这是帝王的待遇。5.“发三河卒穿复士,起冢祠堂”——后世只有张安世获得了这样的待遇。6.“置园邑三百家”――这个就厉害了,空前绝后!按例制,皇后的父母的园邑是二百户,霍光这个园邑搞了三百家。也就是说,霍光的丧事实际上按照天子或诸侯王的标准来办理的。那诸侯王能享受到这个标准吗?在西汉时候,各地诸侯王们“宫室百官”拥有“同制京师”的特权。作为天子之制的“黄肠题凑”的葬制,诸侯王也可以合法享用,但等级、规格和大小各自不同。即然丧事规格达到这个标准,史家若再称之为“卒”,那就欲盖弥彰了。于是,就采用了“薨”这个给诸侯王去世所用的字眼。那么,我们再来看看霍去病去世以后所享受到的殡葬规格是怎样的。相关的记载,咱们先来看一下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:霍去病的死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是用了“卒”这个字眼。大家都知道,霍去病是汉武帝的心腹爱将,像儿子一般的呵护宠信,霍去病之死,令汉武帝如摧心肝。那么他又是怎样为霍去病的丧事规格呢?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有记载:汉武帝把边境五属国的汉胡将士调到关中,让数万兵马穿着玄甲,排列成阵,从长安一直排列到茂陵(汉武帝为自己所建的陵寝),一路护送霍去病的灵柩往墓地安葬。以甲士送葬,这是诸侯王的礼遇,普通大臣是不允许用的。也就是说,霍去病的葬仪也是按照诸侯王的规格而进行的。那为什么司马迁记载霍去病的去世,没有用“薨”而是用了“卒”字呢?这就是史家表达自己观点的笔法。司马迁这个人我们都知道,他的性格坚执不屈,秉笔直书。在他的心目中,霍去病虽然功高盖世,但他终究是大汉的臣子,丧仪的规格并不能改变他的身份。通过前面的“卒”与后面的丧仪规制进行对比,我们知道,这是不符礼制的。也就是说,司马迁认为,汉武帝搞的这个丧仪是“僭制”了。那么在《汉书》中,班固又是怎样记载霍去病的去世呢?在《汉书·卷五十五·卫青霍去病传》中是这样记载的:班固仍然使用的是“薨”字。而这个“薨”字与后面的丧仪对比,是符合的。也就是说,班固认为,以霍去病的功绩,汉武帝给他以诸侯王的丧仪待遇是合乎规制的。同样,再来看看关于汉武帝的另一位大将卫青的死亡。《汉书·卷五十五·卫青霍去病传》这样记载:班固比较有意思,在前面使用的是“薨”,而后面又用了“卒”。看来,能猜测到,卫青的丧事规格是不如霍去病的。原因大家也明白,政治形势已经与以前大大不同了。而司马迁对于卫青的去世仍然使用“卒”字。在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中这样记载:现在的卫青墓就比较寒酸了,给大家放个图:以前还有个碑,由于遭到了一些人的破坏,有关部门就把这块碑给搬走了,原先那块碑就在下图的坑坑位置上。据说是,有个女作家,写了个作品,在她的作品中,把大将军卫青设定成了一个反面角色,她的粉丝们就恨上了卫青,愤怒之下,组织了一帮人,专程去破坏了卫青的墓。这也很无奈,任何时代都不缺少这种无知的鼠辈。现在网上不也有大批为盗掘清东陵的孙殿英大声叫好的蠢货吗?相对来说,霍去病的墓情况稍微好些,是这样的:但比起关羽、张飞的墓来说,差得太远。有时候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,国人的思想真是让人搞不懂。也许是大家更喜欢传说吧。